
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
阿喆、王欣桐和李悦飞,这几个月一直处于等待中。
因没法及时赶回北京,阿喆3 月份被公司辞退。失业 2 个月,他始终瞒着亲人。母亲发来家里小猫的视频,说:“猫瘦了,又不吃东西了。”他总是等到很晚才回复,装出一副还在上班的忙碌样。
工作找了 2 个月,王欣桐还没遇到合适的。疫情前,她辞了工作去澳洲旅行。按照她的设想,早在3 月就该觅得一份正职,但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。2 月至5 月,除了下楼取快递和在小区散步,她都不出门。断了社交,不用搭地铁和吹办公室空调,王欣桐眼角的干纹不见了,早前晒得黯淡的脸、手和腿,也捂白了 40%。
李悦飞正月初六便回了北京。他在东二环银河 SOHO 内的一家简餐店做后厨。那时,北京还没要求隔离。一晃到了 4 月,店铺没开,他却接到了老板打来的停业电话。

从春节到4月,阿喆一直被困在山西晋中老家。
2015 年,阿喆进入一家小型文化公司。他喜欢创作,尤爱填词。听到喜欢的旋律或沉浸在某段回忆中,突然来了灵感,他会立刻将词记在手机便签上。涉足娱乐营销行业后,他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。
春节前两天,老人过世,他赶回奔丧。过年时,正好有一部电视剧播出。作为一家影视营销公司的策划经理,阿喆在家一天也没闲着。

外婆家门口的梨树,小时候外婆经常抱着他坐在树荫下乘凉。

家乡的天空。
早上一睁眼,人还躺在床上,已开始工作。电视剧播出期间,阿喆安排写手和美工提供文案和图片给美食的、娱乐的、美妆的等合作渠道,还负责艺人、综艺的提案等。“每天都在做事,没有周六日一说。”晚上10点,母亲不解地问:“怎么还开会呢?”阿喆答:“我们经常半夜开会,别说晚上了。”这样的状态持续到 3 月,他被迫离职的时候。
3月的第三个周五,阿喆还在为两个电视剧写不同方向的策划案,接到了工作群里的通知:从本周一开始,没有回北京的员工都算请假,工作照做,但工资停发。阿喆认为公司的做法不合适,大家已经干完了一周的活儿,付出了劳动,却没有薪水,而且由于村庄封路,交通阻断了。他在群里质问了一句,不久,便收到了人事发来的私聊消息:“试用期结束,请提出离职”。
阿喆听到公司的决定,生气却无可奈何。每天在家抱着电脑,该做的事一样没落下,“方案我写得挺不错的,也不知道为什么被辞退。”除了他,还有一个正式员工也提出了质疑。“或许他们认为我把群里的氛围带坏了。”
去年 11月,他跳槽到了这家行业内口碑不错的营销公司。总公司做电影营销起家,后来涉猎电视和综艺,成立了子公司。“我加入的是子公司,只有二三十号人,经常有人入职和离职。”阿喆负责电视剧、综艺和艺人的宣传。
娱乐营销行业没有加班费一说,通常是调休。这家公司上下班不打卡,没法计算加班时长。阿喆待过不少公司,“哪怕业务真的很忙,但家里有事,还是可以调休,但这里就不可以。”他经常周六上午被叫到公司开会,开着开着就到了晚上十点;出差也总占用双休日。
2019年,影视行业遭遇一轮寒冬,不少公司关停了。“今年赶上疫情,雪上加霜。”电影停摆,总公司的同事只领 70%的薪水;电视剧这边有活,没有降薪,但他还在试用期,薪水是同事的八成。
阿喆清楚记得他是去年11 月 13日入的职。“谈好的 3 个月转正,但合同上写的却是 6 个月。”签协议时,他没在意,留下了漏洞。2 月受疫情影响,他没有提转正的事;3 月初向人力资源的同事提了,但对方表示还要等人事总监面谈,再无下文。试用期的员工,没有任何保障,即使找仲裁,阿喆也觉得于事无补,“没办法,只能认了。”
4 月初,阿喆搭亲戚的顺风车,从山西回到北京的出租屋。
由于有皮肤疾病,从去年 5 月起,阿喆每周定期去医院做2至 3次 皮肤光疗。之前上班时,看病得挤时间。如今失业在家,倒是有时间错峰看病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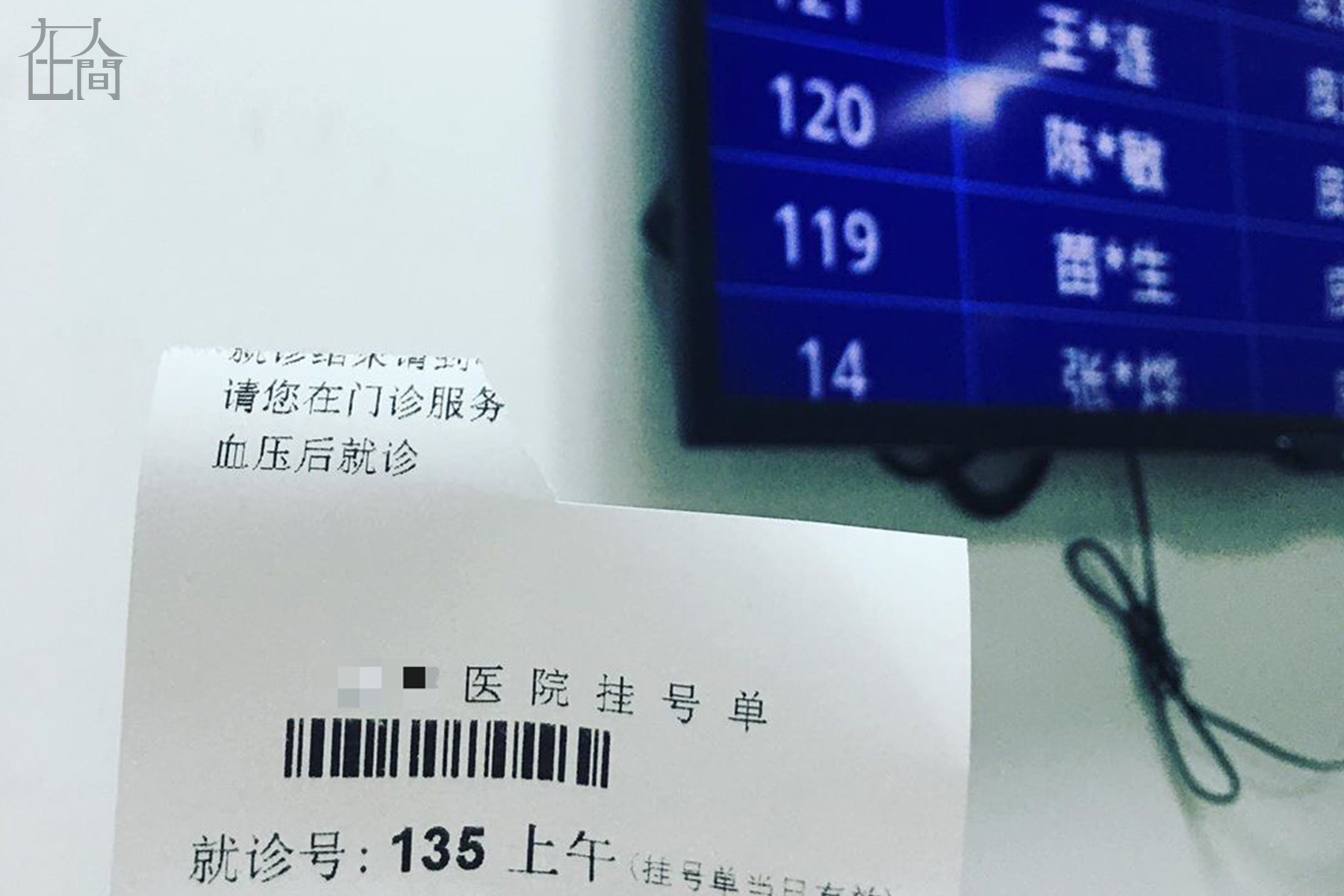
门诊排队等待中。
由于疫情关系,阿喆离职的公司申请了社保延缴。4 月还可以报销,等五一假期后,他去挂号,窗口告诉他“社保卡不在红名单了”。这预示着他的社保断缴,即使补缴,也要等 1 至3 个月才能恢复。以前挂号 10 元,现在每次 50 元。“每周要多花一些钱,还挺困扰的。”
匆忙下,他找了一份品牌策划的工作。阿喆以前做的项目偏娱乐性,这次是为一个二线茶饮新品做推广,“我按娱乐项目做的,感觉效果不好。”在这家公司,他不仅负责策划和文案,工作内容还包括统筹、拍摄等,“整个过程很慌”。工作了一周,经常加班到凌晨 1 点。
加班期间,阿喆认真地考虑过要不要卖煎饼。“朋友觉得我在开玩笑,但那一刻我真的好累,我的脑子快炸了。”他不想再用脑子,哪怕做苦力活。于是,他辞职了。
以前跳槽,两周就能找到凑合的工作,但这次他已经投了一个多月简历,还没有回音。“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,在将就的公司将就着,自己不痛快,公司的活也做不好,两方面都不太行。”曾经只要是感兴趣的、做得了的,阿喆都会投。“现在稍微耐心一点,哪怕耗费一些精力和财力,反正豁出去了。”
同龄的朋友不少结了婚、生了子,娃娃都几岁了。他们在机关或事业单位上班,相对稳定。“有时候觉得在机关工作挺好,加上我是巨蟹座,还蛮需要安全感;但有时候又觉得这么过一辈子挺无聊。”

王欣桐是主动辞职的。疫情暴发初期,她正在澳大利亚享受自己筹划多时的“间隔假期”。
北京奥运那一年,王欣桐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;毕业后,定居北京。10年来,她一直从事农业和公益领域的工作。
2019 年 9 月,她辞去了香港某公益机构项目总监一职,“工作周期比较长,是我离职的一个原因。”项目在乡村,需要配合农户的时间。早上 6 点到现场,等人家不忙的时候,她和团队开始工作;待到晚上七八点,和农户吃完饭,还要继续下一步的工作,十一二点才能回到住宿的地方。一个月出差 20 多天,哪怕凌晨一两点到家,第二天依然按时上班。“感觉不到生活了。”回到家,绿植牺牲很多,“吃不好,休息不好,很沮丧。”
状态不佳,王欣桐给自己计划了一个间隔期,学习、休息和养生:10 月,先到东南亚参加青年交流项目;1 月,到澳大利亚探访亲友;2 月回国;3 月,重新走向社会。“年后是换岗的高峰期,怎么着,20 天也搞定一份工作了”,当时,她还比较乐观。辞职做了顾问,虽然报酬少了四分之三,但工作形式灵活了。
1 月初,王欣桐跟着姑姑、姐姐一起,到澳洲体验生活。澳洲的阳光和空气舒服,语言环境也好,她打算多待些时日,练习口语。那时,谁也不清楚疫情会发展到何种程度。“从 2003 年的 SARS到 2015 年的 MERS,疫情都有一个规律,秋冬开始,来年春天基本就消失了。”王欣桐盘算着从澳洲回来,疫情将迎刃而解,不会对生活和工作造成影响。

澳大利亚的海边。

澳大利亚国家公园里慵懒的袋鼠。

喂袋鼠的游客。
2 月初,航班调整了起飞时间,但王欣桐并没有收到通知。同时,南澳首府阿德莱德确诊了两个病例。王欣桐感到恐慌:“他们去过的地方,我们也去了。”连续 3 天,她不再出门,担心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感染。
正是在此期间,她发现航班变动越来越频繁。除了 9 号和 10 号的航班,之前和之后的全部取消。她决定趁早回国:“如果疫情严重下去,可能回不来了。”她订票时,含税价一张 4500 元;等到临走时再查,同一个航班已经涨到了 42000 元。
2 月11 日,王欣桐踏进了家门。绿植枯死了,多肉植物残存着。鱼缸里的水像苹果味的喜之郎果冻。唯有栽在阳台上的番茄,一个月没人照料,居然红透了一串没烂,出乎她的意料:“我把那几个番茄摘下来,一个一个吃了,糖酸比正合适,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番茄。”

王欣桐自制的午餐。
从去年 12 月起,王欣桐有一搭没一搭地找工作,一个月看两次,了解就业行情。到了4 月,她开始密集地上网,与猎头沟通,“挺意外的,岗位很少”。
年龄也是一道坎。机构合适,岗位又基础,“年纪大了,不愿从基层做起,有点尴尬”,王欣桐说。疫情是一个锅,问题经由它加温,全暴露了。
她从没有过长达 8 个月的职业空窗期。

李悦飞18岁出来做事,在唐山卖过五金、往钢厂送过货,也在天津的电子厂打过工。20 多岁,父母怂恿他进服装厂,那里女孩多,还都是一个村的,方便找对象。闲着没事,他爱跟朋友喝酒,没把心思放在找女友上。
做了一阵子,李悦飞适应不了工厂的生活,“过一年和过一天没区别。”从此,他没再进过厂。2013 年,经朋友介绍,他去了天津一家连锁西餐店,接触到了披萨。“我还以为披萨是火枪烤的,到了才知道是用电烤箱。”
西餐厅的后厨整洁干净,不像中餐厅是火又是烟。渐渐地,李悦飞喜欢上了烤披萨、煎牛排。这是他做得最久的一份工,持续到了 2018 年。之后,他辗转了几家披萨店,再经朋友介绍,应聘上了北京一家简餐店的后厨。

店铺试营业期间的工作照。
店铺筹备时,李悦飞便是其中一员。从早上 9 点工作到晚上8点,他负责备菜、出餐等,周日有一天假期。一个月工资 6000 多块,包吃包住。新开的店铺没有名气,生意冷淡,后厨清闲。李悦飞报了楼里一家吉他社的课程。在歇息的下午,他常坐在厨房的休息区,弹练几曲。
大年三十,他是店里最后一个离开的员工。坐火车不安全,他和同乡商量,租了辆汽车,开了5 个小时,回到老家邯郸鸡泽县——一个产辣椒的地方。
车子租了一周,租期快到时,李悦飞回到了北京。他又成了店里第一个返工的。银河 SOHO没什么人,商铺悉数关着,只有门口的便利蜂开着。门店计划 2 月 8 日营业,实行无接触服务,“老板说延迟几天就正常了。”
李悦飞住在离银河 SOHO仅有 1 公里远的员工宿舍内,偶尔步行去店里打扫卫生、检查消防、清理烂掉的蔬菜。有时候,他也刷个共享单车上街转悠。“街上人少车也少,好多店关着,遇到一个不戴口罩的,赶紧离他远点。”回到住处,除了使劲搓手,他还给鞋子和衣服消毒。

站在店铺门口抬头往上看,是一张巨大的网。
3 月,国内疫情控制住了,国外又严峻起来。“疫情一时半会儿过不去,我想这店开不了了。”
“老家要隔离14天,再来北京还要隔离,干脆不回去了。”李悦飞在北京度过了无所事事的两个月。
4 月 7 日关店后,李悦飞并没有太担心,“关就关呗!这工作不行还可以找别的。”一个朋友在南六环跑快递,买了两辆厢式货车,李悦飞没事做,被叫去跑了几趟,“感觉还不错”。可后来生意直线下滑,一辆车就够拉货,用不上他了。
4 月 18 日,京津冀健康码互认后,李悦飞赶紧回了家。

李悦飞在家已经待了一个月。除了陪亲戚的孩子玩,不做饭也不碰吉他。二弟家的两个,小弟家的三个,大的 11 岁,小的3 岁刚会跑,全跟他闹得起劲。他给他们买吃的、买玩具,还带他们在屋里滑旱冰。开始时小侄子摔了跤,吓得不敢爬起来,后来在沙发和墙角的旮旯里,自己扶着就站起来了。
自从出来打工,李悦飞只在春节回家。父母希望他多待会儿。“今年倒是了了他们的心愿,但再待估计不行了。”他打算等家里的麦子收完,就出门找工作。
以前找工作10天就能解决,最多不超过一个月。疫情下,餐饮行业买卖不好做,普遍下调了工资。李悦飞不想再干老本行了:“前几年喜欢这个,现在觉得没意思。一个月挣个几千块,还不如自己干点什么。”

李悦飞家里收麦子的场景。
鸡泽县属于平原地区,全是一大块的整地。一年种 2 季作物,小麦和玉米轮作。李悦飞家里有 10 亩地。小时候收麦子靠人力,用镰刀割麦子、用麻绳打捆……十天半月才消停。现在人干的活少,除了浇水、打药,其他的工作都用机械,一两天就做完了。李悦飞留在家里,也无多大用处。
在北京租房的阿喆,每天也得往外掏钱。再怎么省,房租、水电省不了。“大部分时间待得住,偶尔还是心慌。大家都在上班,就我每天很闲。”买房的压力、父母逐年老去的压力……他想得比平时多:“我不是积蓄很多的人,父母也是普通人。妈妈没工作,爸爸退休了。我只能靠自己。”
不在外面吃饭,顶多周末与朋友聚聚,阿喆爱窝在家里,看电影、写影评和作词。
在老家,他接到了“某音乐创作大赛”的电话,通知他入围了决赛,但因为疫情,比赛没了后续。小有天赋,却没机遇,作词对阿喆来说,只能是爱好。
他曾改写过一首词:“越走越窄怎么有点无力探出瓶外,含苞未尽酝酿这份期待难盛开,好像我们的爱攀在瓶口徘徊,那些情投意合仿佛没存在。”本是描写两个恋人在谣言和纷争里寻找自己的故事,却应了他当下的心境。
王欣桐曾推荐一位比自己大7岁的老师给猎头,对方直截了当地说“年纪太大”。这句话点醒了王欣桐,“我也将到这个时期,必须做一个决定,选择稳定的还是感兴趣的工作?”她希望找一份做得长久的事业,避免沦落到 40 岁还要跳槽的地步。
好在有积蓄,不至于坐吃山空,加上还有微薄的顾问费支撑,王欣桐找工作的心态得以自洽:“岗位和方向适合我,让我体验到成就感,才是工作。”
不过,在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前,她不排斥兼职。每月光是还房贷、缴五险的支出就超过了 5000元。只进不出的日子,让人心里不踏实。开不了源,她便控制欲望,时不时断舍离一下。前段时间,她在咸鱼上卖了一口锅,进账199 元。

家里的番茄又开花了。
除了浏览招聘信息,王欣桐的时间都用在了开发新技能上——烙饼、煮粥、泡水果茶、做手擀面等。她也舍得花 2 个小时,抽掉鱼缸里的水,给新种的绿植浇上。
虽然种在花盆里的番茄,生存空间小,长不大个,但开春时,王欣桐还是种了几棵:“现在都开花了。”曾给过她意外的番茄,被赋予了新的期待。
以前,王欣桐不喜欢飞机从上空划过的声响,现在有个飞机经过,她还挺高兴的:“说明又有人出差了。”
(应采访对象要求,王欣桐、阿喆、李悦飞为化名)

来源:在人间